六位“白首”文藝家講述“我與改革開放”的故事
原標(biāo)題:盛世看今時 白首猶韶華——“足音”年度回訪·“我與改革開放的故事”特輯

蔡正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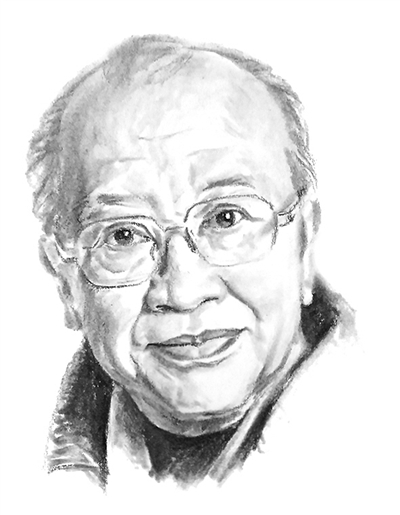
羅錦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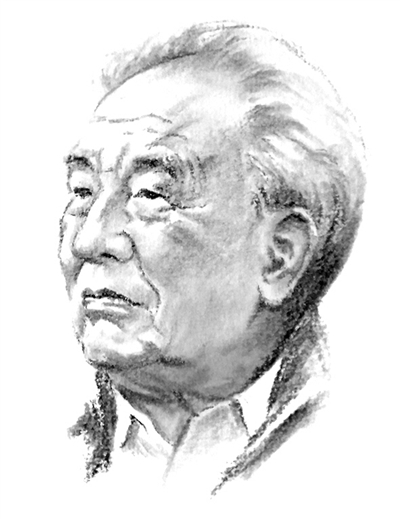
王炳華

李谷一

喬 羽

陸天明
蔡正仁:總持風(fēng)雅有春工
曹玲娟
蔡正仁老師的家,離上海昆劇團(tuán)不遠(yuǎn)。這個周六,蔡老師難得在家。前一晚,他剛從蘇州趕回,參演一臺文藝晚會,清唱了兩段《長生殿》中的《哭像》。此前在蘇州,他一直忙著幫蘇昆排一出新戲,過了這天,還得去昆曲的故鄉(xiāng)昆山舉辦一場講座。
“最近好像是特別忙。”蔡老師笑。排戲,是他第一回正兒八經(jīng)當(dāng)導(dǎo)演,燈光布景都得管。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正也趕上上海昆劇團(tuán)建團(tuán)40周年,上昆要在春節(jié)期間推出系列演出,壓軸的,便是蔡老師等“國寶級”藝術(shù)家領(lǐng)銜的反串版《牡丹亭》。蔡老師反串杜麗娘,老搭檔張靜嫻倒是唱柳夢梅。“難煞我也。”雖有點(diǎn)犯愁,蔡老師又笑著說,“過年嘛,大家圖個開心。”
40年前,恍如昨日。“‘文革’結(jié)束,整整奔走兩年,終于聽到了正式恢復(fù)昆劇團(tuán)的消息。”當(dāng)唱之年,蔡正仁一心想唱昆曲。“文革”期間,他在樣板團(tuán)里唱京劇,硬著嗓子上,“唱的都是夾皮溝老鄉(xiāng)、《紅燈記》里的日本兵……”現(xiàn)在說起來,老兩口還止不住笑。老伴忍不住爆料,“改回昆曲其實很苦的,他都不講。要把粗嗓再改成假嗓,天天吊嗓子硬生生練出來的。”
父親送蔡正仁學(xué)昆曲,還是他年幼時。“我當(dāng)時根本就不知道有昆曲,就問我父親,是不是唱戲時能穿龍袍?”昆曲中,穿龍袍的戲著實不算多,沒想到后來,蔡正仁唱了一輩子的大官生“唐明皇”。
唱了一輩子戲,蔡老師客廳掛的唯一一張演出照,是他與師娘李薔華為紀(jì)念恩師俞振飛同臺演出時的照片。那一年,師娘83歲,蔡老師也有71歲。戲的末尾,師娘跑了一大圈的圓場,末了,氣定神閑,唱完成套二黃唱腔。大幕一閉卻累到只能獨(dú)自站著,不能動,也不肯讓人扶……“你看,師娘那嬌羞的神態(tài),年輕人做不上來的。”如今,師娘的封箱之作,蔡老師掛在最醒目的地方。
與照片隔廳相對的,是俞振飛81歲時揮毫題的字:轉(zhuǎn)益多師與古同,總持風(fēng)雅有春工。蘭騷蕙些千秋業(yè),只在承先啟后中。“俞老師的字很好,很多人上門求字。我倒是沒有開過口。這是1982年我在蘇州昆劇會演時,老師看了我的演出當(dāng)場寫了贈我的。”這幅字,蔡正仁端端正正,掛了30多年。
孫女瀟瀟很有戲曲天賦,蔡老師心里很滿足,當(dāng)年兒子嫌學(xué)戲太苦太累,如今孫女喜歡,他就計劃著要傾囊相授。祖孫倆常常湊一起,研究要學(xué)些什么戲。這幾年,蔡老師的記性是越來越差了,孫女自己動手,在門口給爺爺貼上一張“出門必帶!手機(jī)、電話本、錢、門卡、老年卡”。旁邊月歷下,是蔡老師寫的2018年大事提醒,上面,演出已經(jīng)排到9月了。
羅錦鱗:一生難舍戲劇魂
周飛亞
羅先生記性很好。電話接通,剛報上名字,他馬上想起了我們的上次會面——那是在去年初春,差不多已是1年以前了。他說,“你好你好,好久不見”。
我不禁莞爾。他說起話來語速還是那么快,滔滔不絕,像他鐘愛的戲劇一樣富有感染力。和他談話,你很容易忘記他的年齡。你聽:“近來怎么樣?那事情可太多了,我想想啊——
“去年年底,到河南的三所大學(xué)講了課,這是教育部的任務(wù),‘經(jīng)典藝術(shù)進(jìn)校園’嘛;然后是文化部的‘千人計劃’,面向全國的戲劇院團(tuán)培訓(xùn)人才,這個項目可受歡迎了;1月份剛在國家大劇院開完講座,我的河北梆子版《忒拜城》馬上要開始第十七輪演出了,接下來復(fù)排《晚餐》,這也是第十輪了;哦對了,2月初還要去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講課,天津和河北的學(xué)校也請我去培訓(xùn)師資;今年可能要為國家大劇院排一部古希臘喜劇,我們剛開始商談……再加上博士生的論文答辯,上半年已經(jīng)排滿了!”
這一通介紹,一氣呵成,我都插不上嘴。很難想象,這是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的生活。
羅先生出生時,抗日戰(zhàn)爭正激烈,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直至如今的新時代,他笑稱自己“什么都經(jīng)歷過了”,“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后半生”。
1986年,他在國內(nèi)首次公開排演《俄狄浦斯王》,全國轟動,可以說是他事業(yè)的真正起點(diǎn)。而這正是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機(jī)遇。
“在此之前,一些老藝術(shù)家、包括我的老師,早就想排演了,但這部悲劇的主題是命運(yùn),是‘宿命論’的,在中國比較敏感,當(dāng)時我們是講‘人定勝天’的……再加上毛主席曾批評一些知識分子‘言必稱希臘’,他們就沒敢做。”
羅先生說,其實他內(nèi)心也忐忑。上演后,“觀眾叫好,我不放心;北京市委的領(lǐng)導(dǎo)來看了,都說好,我還是不放心;直到中宣部的同志來看了,也說好,我才徹底放心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二兩酒!”
羅先生覺得,提到改革開放,也許人們的第一反應(yīng)會想到物質(zhì)生活、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巨變,但他更看重的是精神層面。“思想也開放了,國家也意識到這些世界文明瑰寶的價值了。”
后來,劇團(tuán)遠(yuǎn)赴希臘演出,讓世界都看到了中國開放、包容的新面貌。著名劇作家、當(dāng)年還是記者的過士行在《北京晚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足球沒出去,戲劇出去了》。
對這個標(biāo)題,羅先生記憶深刻,至今提起來還直樂。我不禁猜想,過士行后來對戲劇產(chǎn)生興趣,轉(zhuǎn)行當(dāng)了編劇,不知道是否也曾受過這件事的一點(diǎn)點(diǎn)影響呢?
命運(yùn),有時就是這么奇妙——尤其是,在我們身處的這樣一個意氣風(fēng)發(fā)的大時代里。
王炳華:瀚海絲路漫求索
楊雪梅
2017年末,在北京大學(xué)中古史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西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九十周年高峰論壇上,意外見到了王炳華先生。他被安排作關(guān)于新疆考古的主題報告——《從高加索走向孔雀河》,這樣寬闊的視野似乎也只有他可以駕馭。
自1960年北京大學(xué)考古專業(yè)畢業(yè)赴新疆工作算起,王炳華先生在新疆作了40個春秋的考古。2000年退休之后,他被請到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西域研究所教書育人。這幾年他筆耕不輟,繼續(xù)沿著西域研究之路,把自己見證并思考的新中國新疆考古事業(yè)講給更多的人聽。前不久,剛剛拿到了中西書局出版的厚厚一本《探索西域文明》,這是王炳華的師友們按學(xué)界慣例為他的八十華誕而組織的論文集,書中有炳華師根據(jù)自己工作日記整理的《考古行腳五十年》,而改革開放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轉(zhuǎn)折點(diǎn)。
40年前的1978年,季羨林、任繼愈先生一起訪問新疆,王炳華陪著他們在烏魯木齊、吐魯番、克孜爾、庫車庫木吐拉考察。“新疆考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備受世界關(guān)注;改革開放之后,這種關(guān)注度立刻顯現(xiàn)出來。”
在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之初,樓蘭曾是絲路交通的重要節(jié)點(diǎn),但由于種種原因在4世紀(jì)以后便衰落了,古城也隨之消失。1901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重新發(fā)現(xiàn)樓蘭古城,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我國考古學(xué)家黃文弼于1930年曾到達(dá)羅布泊北岸的土垠遺址,但因為湖水暴漲而未能進(jìn)入樓蘭古城。新中國成立后,羅布泊成為軍事禁區(qū),樓蘭考古再次沉寂。直到1979年,中央電視臺與日本NHK合作拍攝《絲綢之路》,王炳華受命帶隊進(jìn)入羅布泊,才有機(jī)會重新走進(jìn)樓蘭。
1979年底,王炳華在位于羅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發(fā)現(xiàn)了古墓溝墓地,墓葬出土的文物證明早在3800年以前的青銅時代就有人類在這里生活。因為這一發(fā)現(xiàn),羅布泊和古樓蘭成為那時世界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80年代末,國家有關(guān)部門表示,在條件合適時,可以考慮與外國合作進(jìn)行考古發(fā)掘。之后才陸續(xù)有了中日尼雅考察、中法克里雅考察等。”他幾乎參與了20世紀(jì)90年代新疆考古全部的重要發(fā)現(xiàn)。
王炳華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跡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緣各綠洲、羅布淖爾荒原、吐魯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綠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相關(guān)的著作更是廣受矚目。在他看來,新疆的考古,從來不獨(dú)屬于新疆。早在張騫鑿空之前,就有一條“史前絲綢之路”的通道存在,對于它的了解完全依賴于考古發(fā)現(xiàn)與科學(xué)研究。“如今有更多的科研機(jī)構(gòu)同時在新疆從事考古,越來越多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不斷填補(bǔ)著時空上的缺環(huán)。在響應(yīng)‘一帶一路’倡議時,因為會涉及許多的國家,許多的民族和地區(qū),考古所揭示的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必定有值得我們今天汲取的地方。”
李谷一:歌聲乘著春風(fēng)來
任姍姍 姚琬昱
穿著家常的衣服,黑發(fā)精致地挽成一髻,坐在面前的李谷一不同于舞臺上的流光溢彩,卻如冬日陽光般讓人親近。她手捧一杯清茶,眼角的笑意和清脆的話語,伴隨茶香熱氣升騰起來。這是李谷一家的客廳。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里的“三多”:鮮花多、陽光多、故事多。一如舞臺下的她。
如果說每一個從上世紀(jì)80年代走來的中國人,心里都流淌著李谷一的歌聲,這并不夸張。“文革”后,中國電影打破樣板式的千人一腔,電影中李谷一的深情歌唱應(yīng)著人們心中的春風(fēng)解凍。她獨(dú)特的氣聲技巧,是帶有先鋒意味的大膽嘗試。一首《鄉(xiāng)戀》,引發(fā)了新舊兩種文藝觀念的激烈論爭。“俗話講無聲勝有聲,《鄉(xiāng)戀》像俯在耳畔的竊竊私語,是飽含情感的娓娓道來,富有人情味,‘你的聲音你的歌聲’——”她一邊唱,一邊做解釋,有的歌唱的時候用“全氣”,有的用“半氣”。你能感受到,每一處氣息和吐字都有極為講究的力道。
1983年央視首屆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觀眾通過熱線高密度點(diǎn)播,導(dǎo)演組遞了好多輪條子給在現(xiàn)場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鄉(xiāng)戀》終于在春晚得以“正名”。那個大年夜,包括《鄉(xiāng)戀》在內(nèi),李谷一唱了9首歌。她的歌聲乘著春風(fēng)而來,里面有觀眾潮水般的期待,也有一個時代對文藝的召喚。
“邁出第一步總是難的。”再憶那暴風(fēng)驟雨般的過往,李谷一有了更深沉的感慨,“我們的文藝應(yīng)該以人為本,歌始終是唱給大眾聽的。”
《鄉(xiāng)戀》之外,諸多閃光的“第一”刻度了李谷一的藝術(shù)人生。比如,1982年李谷一著手創(chuàng)建中國輕音樂團(tuán),擔(dān)任團(tuán)長的她爆發(fā)了強(qiáng)烈的創(chuàng)作力,《難忘今宵》《故鄉(xiāng)是北京》《前門情思大碗茶》《我和我的祖國》等傳唱整個中國。再比如,90年代初,她根據(jù)自己的藝術(shù)實踐首次提出“戲歌”的概念,一直影響至今。
六十載如白駒過隙,光陰載不走的是為人民為時代歌唱的情懷。半個月前,李谷一和新生代歌手霍尊合作演唱了《一念花開》,這首古香古韻中國風(fēng)的歌曲一上榜就贏得了不同年齡觀眾的心。“點(diǎn)擊率相當(dāng)高”,頗感欣慰的李谷一用手機(jī)播放給我們聽,她的歌聲如同擺脫時間的重力,青春依舊。“現(xiàn)在的歌曲激烈豪爽的多,抒情細(xì)膩的少。大刀闊斧容易遮蓋細(xì)膩的東西,抒情歌曲在處理時更要細(xì)細(xì)琢磨。”
雖年過七旬,但李谷一從未停止對藝術(shù)完美的追求和嘗試。《山水》《龍文》《一路芬芳》《那溪那山》《大好河山耀中華》《你不來船不開》《牡丹獎之歌》……最近一兩年,她接連捧出這些新作。在一些社會活動中,她為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出中肯的建議,經(jīng)她指點(diǎn)的一些“好苗子”,也接連在音樂比賽中獲得大獎。
“唱《鄉(xiāng)戀》時,我根本想不到文藝能像今天這般百花齊放。”回首40年風(fēng)起云涌,李谷一感慨萬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diǎn),她仍在思考:如何繼續(x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如何用更多好作品回報新時代。
喬 羽:歌詞就是家常飯
任飛帆
“不要叫我喬羽老師了,就叫我喬老爺吧。”
聽到這個稱呼,我一下子樂了。熟悉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的第三個名字。上世紀(jì)60年代,電影《喬老爺上轎》十分轟動,身邊的朋友覺得喬羽酷似主人公,剛好也姓喬,于是漸漸叫開了,連周恩來總理都公開叫他喬老爺。對此,他一直洋洋自得。
喬老爺一生創(chuàng)作無數(shù),膾炙人口的歌曲有幾十首。有人開玩笑說,喬羽創(chuàng)作了三大“國唱”:《讓我們蕩起雙槳》是寫給少年兒童的,《夕陽紅》是寫給老年人的,《我的祖國》是寫給所有中國人的。
2016年底,臺灣作家龍應(yīng)臺在香港大學(xué)做講座時,問臺下觀眾的啟蒙歌曲,校長回答《我的祖國》,于是,現(xiàn)場零零星星響起“一條大河波浪寬”,緊接著演變成全體大合唱。那個場景,感動了看到視頻的每一個人。記得這件事發(fā)生不久,我正好有機(jī)會拜訪喬老爺,于是很激動地把那段視頻播放給他看。他卻很平靜,只是淡淡一笑,“那么多人現(xiàn)在還在唱我的歌曲,我很高興。”
想來,類似的場景,喬老爺應(yīng)該見得多了。無論是每年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壓軸歌曲《難忘今宵》,還是奶奶的《人說山西好風(fēng)光》,媽媽的《思念》,甚至我兒時的《大風(fēng)車》《小哪吒》,喬老爺?shù)母枨擅畹刎灤┝松臋M軸和縱軸,伴隨著一個人的成長軌跡。
“我素來不把歌詞看作是錦衣玉食、高堂華屋,它就是尋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飯、粗布衣,就是雖不寬敞卻也溫馨的小小院落。說到底,寫歌詞要從自己的經(jīng)歷出發(fā),沒有真切體會是寫不出好歌詞的。”這就是喬老爺歌曲創(chuàng)作的準(zhǔn)則,也是他的歌曲被一代代人傳唱至今的原因。
在他看來,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的歌詞創(chuàng)作出現(xiàn)過三次高潮:一次是在抗日救亡運(yùn)動之時,大批抗戰(zhàn)歌曲成為抗日救亡的戰(zhàn)鼓和號角,激發(fā)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一次高潮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詞作家和作曲家把人民群眾翻身解放的喜悅寫進(jìn)了歌曲;再一次就是從改革開放之后的80年代開始出現(xiàn)的并持續(xù)至今。
“改革開放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給藝術(shù)家?guī)砹烁訌V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新的觀念、新的思維讓我們在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同時擺脫了歷史的羈絆,無數(shù)反映新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脫穎而出。可以說,這一次高潮持續(xù)的時間最長,產(chǎn)生的作品最多,作者的隊伍最大。”我想,喬老爺后來的《難忘今宵》《愛我中華》,大概都是在這種時代氣氛感召下寫成的吧。
陸天明:文學(xué)當(dāng)參與時代
康 巖
陸天明老師家在北京昌平,一幢二層高的白色小洋樓。推門而入,他正端坐在沙發(fā)上讀書,老花鏡穩(wěn)穩(wěn)架在鼻梁上。我瞥了眼書的封面,是村上春樹的《1Q84》。
注意到我的目光,他笑笑說,“讀書口味要雜一點(diǎn),年輕人喜歡的,我也想看看。”
去年底,他的長篇小說新作“中國三部曲”第一部《幸存者》剛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按計劃應(yīng)該超過百萬字,寫完估計就沒氣力了,應(yīng)該是我最后的長篇。”一說起作品他就興奮,身子微微前傾,還帶上小幅度的手勢擺動。
《幸存者》把指針撥回40年前,主人公們——按照陸天明的定義——應(yīng)當(dāng)是中國最后一代“理想主義者”。“每代人都有理想。今天談理想更多是個人生涯規(guī)劃,想當(dāng)科學(xué)家、企業(yè)家。我寫的這代人中的某一群人,是以革命為理想,要走到最邊遠(yuǎn)最窮苦的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一起改造中國。”
“這代人”也包括了他自己。兩次主動要求上山下鄉(xiāng),也經(jīng)歷過政治動蕩,陸天明回過頭來書寫這一代人的時候,帶上了自身的生命體驗。直到改革開放后,生活迎來新機(jī)遇,創(chuàng)作也開辟了新天地,尤其是電視的普及,讓他在小說、話劇的基礎(chǔ)上又開始了電視劇創(chuàng)作。
乘著電視熱的東風(fēng),陸天明當(dāng)年憑借《蒼天在上》和《省委書記》的出版及電視劇改編,平地驚雷般,炸開了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反腐敘事。也正由此,他一直被貼上“反腐作家”的標(biāo)簽。“剛開始我不愿意,后來漸漸習(xí)慣了。反腐也可以寫得很文學(xué),關(guān)鍵是要為老百姓說話。”
陸天明提倡的是“參與文學(xué)”。當(dāng)下中國已經(jīng)走進(jìn)新時代,那場始自40年前的偉大變革仍在持續(xù)發(fā)酵,并在進(jìn)一步深化,從而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民族的未來。作為社會群體中最敏感的神經(jīng)末梢,面對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作家不能視而不見。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歷史的使命,更是作家良知和良心的呈現(xiàn)。
“中國三部曲”的創(chuàng)作,正是為了響應(yīng)他內(nèi)心的呼喚。此外,他還忙著創(chuàng)作一部表現(xiàn)港珠澳大橋設(shè)計的電視劇,著力表現(xiàn)“大國工匠”們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締造偉大工程、實現(xiàn)中國夢的努力。
離開時,我們互相加了微信。翻開他的朋友圈,里面都是對當(dāng)今時事的轉(zhuǎn)發(fā)點(diǎn)評,也有推介自己作品。有一條這么寫:“偶爾看到豆瓣對《幸存者》的評分,8.7,給出評價的大部分都是年輕的讀者。”言語間倍感欣慰。
老驥伏櫪,壯志凌云,祝愿陸老師生命常青,文學(xué)生命常青。
(版式設(shè)計、人物速寫/蔡華偉)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jī)+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