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紅色主題美術創作的時代活力
近年來的紅色主題美術創作,從作品創意、構圖與色彩的表現,到中國本土藝術趣味的強調,涌現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當代主題性繪畫、雕塑等美術佳作。在取得成績、獲得好評的同時,問題和困惑也與進展并存:與以往的主題性經典作品相較,我們今天的藝術風格特征有哪些新變、還缺少點什么?哪些方面已經超越了前輩,哪些方面值得投入更大精力?如何用新形式、新風格以及新媒介材料來表現紅色主題?這些都成為當下主題性美術創作的核心課題和學術突破點。

董卓《科教興國戰略——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美術作品展覽”陳列作品)
通過視覺象征塑造民族精神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回首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生活在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發展變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和現實價值。尤其在美術領域更是如此,因為美術創作最能敏感、直接地反映社會時代的發展變化。當我們聚焦重大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作品的時候,用“紅色主題美術”這一詞語來進行概定和審視,在紀念建黨百年之時具有特別的文化內涵和現實意義。
20世紀初以來,無論是左翼美術家聯盟的成立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都強調了文藝作品對于民眾革命意識的激發;無論是早期的延安木刻,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人物畫和山水畫創作,都深刻呈現了民眾的精神回應,其背后所涌動的,既有社會發展變化中深刻的集體意志,也是每個藝術家個體內在的精神旨歸。從20世紀上半葉一直到今天,紅色主題美術創作的發展脈絡中涌現出如此多的經典作品,對于塑造各個時期的民族精神,特別是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影響主要呈現為三個方面的內容趨向:
其一,力求抓住時代焦點,凝聚社會民心。無論是抗戰時期批判侵略者、歌頌大后方的勞動建設以求激勵斗志,還是反映改革開放以后打開國門、面向全球化視野之后的新經驗,緊跟時代的美術創作都在潛移默化中真正起到了緊扣時代脈搏、聚攏民心所向的社會作用。
其二,通過視覺象征寓意,塑造民族精神。美術作品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其在視覺呈現角度上的可見、可感、可讀,能夠相對直接、聚焦地表述一種態度或呈現一種氛圍,這就顯現了視覺藝術的獨特作用。視覺的象征性、寓言性,對于時代精神的塑造往往會產生直觀而有力的建構作用。
其三,以個體之眼觀照家國社會,建構審美共鳴。在大眾傳播層面,紅色主題美術作品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雅俗共賞,就是因為這些作品扣動了人們的心弦,找準了社會發展的脈搏和集體審美訴求,這種能夠引起民眾共鳴的時代觀照本身,即是一種帶有社會使命和文化擔當的藝術呈現,同時又抒寫著創作者個人的情感脈動。
藝術創作是歷史真實的升華
紅色題材美術和主題性美術創作中,歷史文獻本身的文學性表達和創作圖像的感性視覺因素之間往往呈現為一種互動關系。特別是面對敘事性的圖像,能否有效地、巧妙地凝結和呈現一個意涵豐富的意象瞬間,最終考驗的是藝術家的智慧及其駕馭圖像敘事的本領。
西方的經典主題性繪畫作品如達維特的《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畫家選取拿破侖從教皇手中接過皇冠給約瑟芬皇后戴上這一戲劇性瞬間,表現出強烈的敘事張力,同時又在歷史感和藝術性之間找到了最為恰切的表述點。中國的紅色主題美術創作中也有這樣經典的案例,如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壯士》選擇了英雄們跳崖犧牲前的一瞬間,以金字塔式的構圖、紀念碑式的人物群像,呈現英雄們面對殘暴敵人時寧死不屈、頂天立地的氣概;何紅舟、黃發祥的《啟航——中共一大會議》,以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李達等一大代表正在登船的場景,再現中共一大南湖會議的歷史瞬間,畫面選擇的光線、角度、人物姿態與情緒的具體表現,都來自藝術家主體對于歷史的理解。

詹建俊《狼牙山五壯士》(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正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美術作品展覽”中,諸多尺幅巨大、描繪人物眾多的黨史題材美術作品,連同黨史館廣場前《旗幟》《信仰》《偉業》《攻堅》《追夢》五組大型主題雕塑,都以視覺形象的方式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奮斗歷程。這些美術作品都在敘事性的視覺形象表達中,展現了這種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之間的契合關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二者之間不是嚴整對應的,而是滲透激發的關系。藝術作品不能片面地從圖解歷史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藝術創作,藝術創作依然要在現實之上,展現藝術本身升華性的詩意和感召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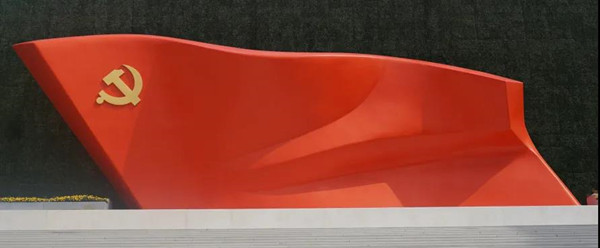
雕塑《旗幟》
與文學創作的意象性相比,美術創作對于歷史真實的視覺細節更為依賴,但是對于審美感性的側重和對于觀者接受趣味的考量,也應成為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美術創作的重要取向。這一點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看,可能會看得更為清晰透徹。筆者前段時間重讀余華的小說《活著》,他是用文學的語言展現了某種生活意象,即中國人的韌勁和對于生命的理解,而這種意象的表達是不露聲色的。如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講述了主人公福貴和老黃牛在晚霞之中的場景,這就呈現為一個生動可感的畫面,中間有曲折的敘事,但回過頭來品味,這個瞬間場景又是最為深入人心的意象。主題性美術創作也是這樣,一件作品最后帶給觀者的雖然是一個物質性的、具體的畫面或作品實體,但最重要的是其呈現出了什么樣的意象,這個意象本身就連接了圖像和文獻,連接了藝術和歷史、感性意識和邏輯判斷。
紅色主題美術創作的當代拓展
在新時代的文化背景之下,我們面對的時代主題、社會語境和文化氛圍,已經和既往的20世紀拉開了距離。老一輩藝術家的作品在成為經典的同時,也為后來創作者樹立了高標準,設置了學習、超越的難度。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反思: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主題性創作開始陷入一種模板化定式的風險,從原來真摯鮮活、接地氣的創作風格,蛻變得在用圖像講故事和敘事抒情時總有力不從心之感?而事實上,以自然的、富有人性的、放松的方式講述故事、抒發情感、表述意趣,對于藝術家來說首先是權利,反過來也是職責。既要專業圈里“叫好”,又要觀眾群里“叫座”,自我表現與社會共鳴是衡量一件作品的兩把標尺。美術家作為一個時代最為敏銳的觀察者和形象塑造者,應該有勇氣和能力挑起這份擔子。在主題性創作的理論研究層面,我們同樣呼喚貼近創作本體的、能夠經世致用的研究,避免理論觀念過于玄虛化、空洞化,這也是對于主題性美術創作在今天的觀望與研究的一種反省和建構。
時至今日,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偉大時刻,新時代的紅色主題美術創作也面對著新的時代課題。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命題,還是要進一步深入生活,抓準時代脈搏,這對藝術家來講又是最重、最難的一道題。無論是面對既有創作命題,還是直面鮮活真切的時代生活,畫什么?怎么畫?為什么要這樣畫?要想抓住、抓穩、抓準時代脈搏和主題要義,就得要深入生活,先破題,判斷這件作品最核心的表現點和突破點在哪里。而要做到這些,無疑需要創作者有付諸實踐的、深刻敏銳的生活體驗。為此,我們不應滿足于傳統意義上慣常的表現方法,在這個基礎之上要有當代性的拓展,即在觀念、題材和表現手法上隨時代而拓新,不能滿足于過去的既有表現形式和創作范式,當前有很多新人、新事、新氣象,都值得我們去感知和表現,這就要靠藝術家敏感的眼睛、溫潤的心靈和創造性的手法去實現。
歸結起來,要突破觀念與媒介的局限,真正實現紅色美術創作的當代性拓展,不僅僅要擴展作品尺幅、強化視覺張力,還要讓觀者心生感動,在品味圖像后有所感悟。這當然是高標準的要求,但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與終極追求。這就需要更多的高水平藝術家能夠投入到主題性美術創作的領域中來,尤其是更多優秀中青年藝術家,以其鮮活的創造力激發紅色美術創作的時代活力。唯其如此,紅色主題美術創作和我們期待中的優秀主題性美術創作才能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涌現出更多不負時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于洋,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