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戰(zhàn)爭系列收官之作《抗日戰(zhàn)爭》出版
每一個年輕讀者都是我的上帝,我就是寫給你們的
王樹增:寫抗戰(zhàn)是寫不屈的民族性格
——王樹增戰(zhàn)爭系列收官之作《抗日戰(zhàn)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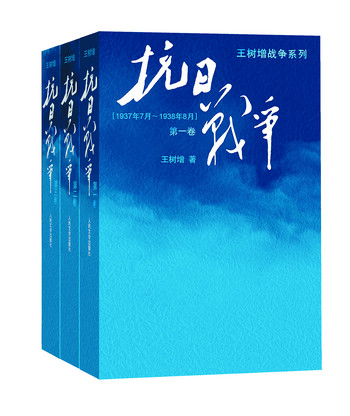
《抗日戰(zhàn)爭》 王樹增 著
王樹增戰(zhàn)爭系列自2006年開始出版,至今已有《長征》《解放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一系列作品問世。他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戰(zhàn)爭史寫作范式,也為戰(zhàn)爭文學(xué)樹立了新標(biāo)桿。
這一系列作品所具備的堅實宏大的結(jié)構(gòu)、國際的視角、對現(xiàn)實的觀照以及詳盡的資料,使他擁有了數(shù)百萬忠實的讀者。《抗日戰(zhàn)爭》第一卷于今年6月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二三卷將陸續(xù)面世,至此,他的中國戰(zhàn)爭系列作品將完滿收官。
《長征》基調(diào)樂觀,以這一人類重大的精神事件展示信仰的力量;《解放戰(zhàn)爭》氣勢恢宏,寫出民心向背之別對戰(zhàn)爭的決定性影響;《朝鮮戰(zhàn)爭》以對萬千戰(zhàn)士的悲憫之情,構(gòu)建起對戰(zhàn)爭整體格局的無奈與戲謔;而《抗日戰(zhàn)爭》基調(diào)莊嚴,全景真實再現(xiàn)了抗日戰(zhàn)爭的慘烈與悲壯,是70年來第一部屬于中國全民族的抗戰(zhàn)史。
“我的作品都是焦灼心靈之下的產(chǎn)物。抗日戰(zhàn)爭是一個寫作的富礦,但如果不是為了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我可能還在尋找,為此我到過日本,到過臺灣,我總覺得倒不是檔案不夠或者是史料不夠,這沒有夠不夠的問題,總覺得還沒有吃透,我總期待我的心理能和那段歷史更加靠近,和那段歷史當(dāng)中的中國人,我們的前輩心靈更加靠近。”近日,繼《朝鮮戰(zhàn)爭》《長征》《解放戰(zhàn)爭》之后,王樹增戰(zhàn)爭系列作品登頂之作《抗日戰(zhàn)爭》與讀者見面,在談到創(chuàng)作感受時,他如是說。《抗日戰(zhàn)爭》是站在全民族抗戰(zhàn)的立場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大背景下,以重大戰(zhàn)役戰(zhàn)斗為軸,以重大歷史事件及相關(guān)人物為經(jīng)緯,全景式地記敘了1937至1945年這八年抗戰(zhàn)中的主要戰(zhàn)役戰(zhàn)斗。
在王樹增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有一個重要轉(zhuǎn)向是從虛構(gòu)轉(zhuǎn)向非虛構(gòu)。作為魯迅文學(xué)院與北師大研究生院共同舉辦的首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研究生班學(xué)員,王樹增和莫言、劉震云、余華、遲子建、嚴歌苓等人曾是同學(xué),有過一段純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他還獲得過曹禺戲劇文學(xué)獎,有人曾拎著一兜錢找上門說,王老師,錢擱這兒了,八個月后,您寫個新劇本,一集多少錢。王樹增說,寫一部戲的錢,老百姓可能一輩子都掙不來,但他回絕了。他跟來人說:你把錢拿回去,我不寫,因為我有我的寫作。他說,現(xiàn)在自己夠吃夠喝,什么都不缺,不玩股票,不搞期貨,要那么多錢干嘛?王樹增有自己的目標(biāo),他認定的寫作,就是在國內(nèi)有些冷落的非虛構(gòu)創(chuàng)作。在他看來,非虛構(gòu)是極其有魅力的寫作領(lǐng)域,只是國內(nèi)太少有人涉足。他說:“現(xiàn)在大量報告文學(xué)、紀實文學(xué)已淪為地攤文學(xué),所謂大揭秘、大內(nèi)幕,只是用糨糊花兩個月時間簡單拼貼出來的,沒有認知上的價值。但是在世界文壇上,非虛構(gòu)經(jīng)典迭出,占據(jù)了大半壁江山,有相當(dāng)?shù)淖x者群。如果誰有志拿起非虛構(gòu)的寫作,就會感到魅力無窮。”從虛構(gòu)轉(zhuǎn)向非虛構(gòu),拒絕了劇本創(chuàng)作的誘惑,王樹增陸續(xù)推出了極其厚重的戰(zhàn)爭系列與近代史系列作品。
不反對娛樂,但祖宗不能娛樂
為什么王樹增說他的作品都是焦灼心靈下的產(chǎn)物?不妨看看他經(jīng)歷過的一件小事。有一次,一家主流媒體的年輕女記者跟王樹增做訪談節(jié)目,問道:“王老師,聽說黃繼光是假的,你作何評論?”一聽這個,王樹增當(dāng)時就火了。他說節(jié)目不做了,咱們PK一下,說說道理。他告訴那個記者:黃繼光不僅是真的,而且還活著。他給了三個理由:第一,43年前,他還是少年時,第一次穿上軍裝,有幸成為黃繼光所在部隊的一員,黃繼光是他的軍中前輩。直到今天部隊點名,還喊黃繼光的名字,全連答到,幾十年如一日。第二,他寫過《朝鮮戰(zhàn)爭》,詳盡地了解過黃繼光為之獻身的國際背景,南北朝鮮都去過;第三,他曾采訪過黃繼光的上下級,包括把他的遺體從山上背下來的志愿軍女衛(wèi)生員。王樹增說,他現(xiàn)在有些后悔,那次錄節(jié)目時干嘛嚇唬一個小女孩?但是他還想說的一句話是,孩子,什么都可以說著玩兒,不反對你們娛樂,但祖宗不能娛樂,這是一條底線。一個有出息、心靈健康的民族,絕不干這種事。
在王樹增看來,人們的生活樣式可以選擇,可以有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這是社會開放、進步的體現(xiàn),沒有問題,但對于國家、民族的忠誠,是個底線,必須守住。王樹增說,無論日本人,還是韓國人,在這方面沒有一絲一毫的含糊,但在當(dāng)代中國,很多人卻守不住。王樹增的親身經(jīng)驗是,雖然日本社會政治文化多元,但無論持何種立場,他們都不允許損害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又比如到韓國,剛下飛機接他的人就說,王老師,聊天時千萬不要說韓國不好,這個話題會引起不愉快。在王樹增看來,底線就是民族的良心和種族的歸屬感。拋棄黨派、政治的因素,一個國家還應(yīng)有一個純凈的底線。當(dāng)代中國一些人連這都守不住,可見思維混亂嚴重。這也是他寫《抗日戰(zhàn)爭》的深層原因,他要反思:一個民族不堅守底線,一旦危難來臨該怎么辦?對于社會上的一些現(xiàn)象,比如現(xiàn)在有人很超脫,說憑什么讓我玩命?生命是我自己的。王樹增說,這就是抓住自己頭發(fā)要離開地球的感覺。真正的中國男人,青年人,要維護父母、孩子不受屈辱,必須當(dāng)勇士,順民都不行,更別說漢奸。
抗日戰(zhàn)爭是一場過于殘酷、過于不公平的戰(zhàn)爭
有人問王樹增,軍事科學(xué)院和國防大學(xué)有那么多軍事研究專家,你憑什么寫戰(zhàn)爭?王樹增回答:“我不是軍事學(xué)家,不是歷史學(xué)家,也算不上學(xué)者,充其量就是一個作家,從事非虛構(gòu)文學(xué)的寫作。我的作品,包括戰(zhàn)爭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實際上是寫一個民族的心靈史。《長征》寫永不言敗,《解放戰(zhàn)爭》寫人民的力量。寫《抗日戰(zhàn)爭》,實際上我有一個強烈的動機,就是寫不屈的民族性格,思考民族之所以有頑強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王樹增說,抗日戰(zhàn)爭對于中國來講過于殘酷、過于不公平。這是兩個國力、軍力十分不對稱的戰(zhàn)爭,和后來蘇德發(fā)生的戰(zhàn)爭還不一樣。當(dāng)時我們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我們處于冷兵器時代。但是日軍是什么?日軍是航空母艦時代。當(dāng)時中國沒有自己的工業(yè),少量的民族工業(yè)非常可憐,是落后的農(nóng)業(yè)國,天災(zāi)人禍頻發(f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低下。再看看當(dāng)時的政治、軍事背景。從民國初延續(xù)下來的軍閥混戰(zhàn)形成了中國當(dāng)時獨特的政治體制和軍事體制,中央只能管一小塊,蔣介石從來不是名副其實的三軍統(tǒng)帥。還有一點很重要,當(dāng)時所謂的中國軍隊,包括有幾輛坦克的中央軍在內(nèi),都缺少現(xiàn)代戰(zhàn)爭觀念。在整個戰(zhàn)爭進程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見死不救、落井下石的情況,有時候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戰(zhàn)爭觀念上的。于是,從盧溝橋事變到第二次淞滬會戰(zhàn),日軍作戰(zhàn)指揮部的戰(zhàn)役規(guī)劃參謀的計算方式是1:10,也就是日軍的一個師團,至少可以對付中國十個師以上,甚至更多,傷亡比例也可以這樣計算。
有個日本歷史學(xué)家曾指出,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軍隊的士兵看上去就是農(nóng)民,沒什么兩樣,日本的農(nóng)民看上去就是士兵,也沒什么兩樣。王樹增非常認可這個說法。中國農(nóng)民,特老實,而且有點兒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那么在面對這場過于殘酷、過于不公平的戰(zhàn)爭時,中國農(nóng)民能否換一種思維方式?王樹增說,實際上在戰(zhàn)爭中,無論將領(lǐng)還是普通士兵,往往做出驚人之舉。他舉了一個小例子。他曾查到一本日本檔案,記錄了戰(zhàn)爭期間的通報,其中講到一個日軍中佐的死亡,讓王樹增吃了一驚。那場戰(zhàn)斗國軍潰敗,遍地尸體,日軍中佐帶領(lǐng)部下,舉槍瞄準遠處的逃兵取樂,數(shù)一二三,打倒一個,再數(shù),又打倒一個。可是正數(shù)著時,中佐自己突然應(yīng)聲倒地。他的部下就納悶了,周圍都是尸體,怎么會中彈?驚愕之余,有一個日軍比較狡猾,一個個摸尸體手中的槍,突然發(fā)現(xiàn)有一個士兵的槍是熱的,但是這個士兵確實已經(jīng)死了。后來王樹增調(diào)查,真在中國的檔案中找到了這個士兵,他是在咽氣前開了最后一槍。寫到這件事時,王樹增說書中有幾句話特別能表達他的心情:除了這個士兵的名字之外,我無論如何查不到這個十幾歲的普通中國農(nóng)民來自何處,家鄉(xiāng)何處,父母是否安在,他的父母是否知道他已經(jīng)倒在了這塊土地上,他的尸骸埋葬在了什么地方。我們只知道一個名字。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座豐碑。王樹增說,這類細節(jié)不能編,只能在檔案中查找。而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個。
在書里,王樹增還用大量篇幅寫到了高校的轉(zhuǎn)移。他說,這部分史料充分,他更多不是記錄過程,而是寫一種精神:當(dāng)侵略者到來時,那些高校師生不愿意以順民的身份在統(tǒng)治區(qū)安放書桌,所以,即使有些教授年歲都很大了,也寧可步行走一兩年到后方去,難道這些師生們不是英雄好漢嗎?王樹增覺得這些人讓他肅然起敬。多少教授和青年孩子就死在半路了,生病、饑餓、被轟炸,而且,他們還扛著儀器,帶著實驗室的設(shè)備。王樹增書中寫到華東的一個農(nóng)學(xué)院轉(zhuǎn)移,為了保護教學(xué)用的兩條荷蘭奶牛,很多師生死了,奶牛卻活了下來,因為它們是實驗用品,荷蘭最好的種牛,這些師生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它們。
王樹增提到,日軍淞滬戰(zhàn)役,無差別轟炸上海,日軍空軍作戰(zhàn)命令中第一批襲擊目標(biāo)就有商務(wù)印書館。日本人說得非常清楚,要想摧毀中國的抗戰(zhàn)意志,必須滅亡她的文脈,將文化連根拔掉,就征服這個民族了。所以,民族精神不死,文化不死,這個民族就打不倒。王樹增說,高校遷徙,正是這樣的意義。
誰拿黨派之爭看待抗日戰(zhàn)爭,就是小肚雞腸
在書里王樹增專章談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探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中流砥柱的問題。王樹增說,關(guān)于“中流砥柱”這四個字,現(xiàn)在也是社會輿論爭論的焦點。他個人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之所以說是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主要的論據(jù)不是軍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至少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當(dāng)時中國一盤散沙。中國共產(chǎn)黨人寧可拋棄前嫌,提倡歸國民政府領(lǐng)導(dǎo),僅僅這句話就很了不起。為什么?當(dāng)時中國最主要的黨派之爭是國共之爭,這是兩個死對頭,但一旦面對強敵,要亡國滅種時,共產(chǎn)黨一方能夠站出來公開說服從國民政府領(lǐng)導(dǎo),服從民族命運這個大趨勢,這對各路軍閥和各路小黨派起到很強的引領(lǐng)作用。沒有萬眾一心,抗日戰(zhàn)爭打不下去,因此怎么評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創(chuàng)造和建立都不為過。
第二個理由,我們現(xiàn)在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依然會佩服這位偉人的戰(zhàn)略思想。他用毛氏文風(fēng)敘述了戰(zhàn)爭的進程,以及每個階段的對策,歷史證明精確無誤。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當(dāng)時蔣介石案頭有這本書,白崇禧等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的案頭也都有這本書。《論持久戰(zhàn)》的觀點是保證抗日戰(zhàn)爭最后取得勝利的關(guān)鍵性戰(zhàn)略思維。
第三個理由就是廣闊的敵后根據(jù)地的建立。論述抗日戰(zhàn)爭的中國戰(zhàn)場,偏重哪一個戰(zhàn)場都沒有辦法解釋戰(zhàn)爭的進程。二者廢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條腿。沒有敵后戰(zhàn)場,正面戰(zhàn)場絕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始終一直在牽制著日本幾十萬的部隊,雖然最后的日軍部隊已不是精銳,全是丙級兵團。為什么呢?日軍主力兵團也不在正面戰(zhàn)場上,跑到緬甸和太平洋戰(zhàn)場去了,守硫磺島去了。但是敵后戰(zhàn)場我們牽扯日軍的兵力沒低過40萬,這個日本檔案有記述的。
“我有一句話,我從來不拿黨派之爭的觀點看待這場戰(zhàn)爭。誰拿這種觀點去看,就對不起我們的先人,是小肚雞腸。”王樹增曾在多個場合說過,如果我們對這場慘烈的抗日戰(zhàn)爭的表述和認知過于狹隘的話,對那些倒在戰(zhàn)壕里的年輕生命是不公允的。這場戰(zhàn)爭是全民族的抗戰(zhàn),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階層、所有的黨派,甚至所有的國際力量,還有那些散落在這個世界每個角落的華僑。這場戰(zhàn)爭牽動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沒有這個前提,沒有全民族抗戰(zhàn)的前提,就不能解釋這場戰(zhàn)爭的結(jié)局。
近年來,王樹增覺得國內(nèi)對于抗日戰(zhàn)爭的看法越來越寬容、開放。他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智慧,贊揚別人不等于貶低自己。用寬容的心態(tài)看待歷史,實際上是樹立自己的人格形象。他說,寫抗日戰(zhàn)爭,站在一個民族的立場上,永遠不會犯錯,永遠是正義的。他現(xiàn)在給讀者提供的是比較公允的立場,比如在作品中很少用共產(chǎn)黨軍隊、國民黨軍隊這樣的詞。這是因為這樣的詞在抗日戰(zhàn)爭中并不存在。抗日戰(zhàn)爭中對中國軍隊的稱呼有幾個:從日方來講,是中國軍隊;英美叫華軍;汪偽政權(quán)建立后,日軍對中國軍隊的稱呼變成兩個,一個是南京軍或者政府軍,實際就是偽軍,另一個是重慶軍,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共產(chǎn)黨的軍隊,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之后,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是在中央政府統(tǒng)轄下的編制中的一支。共產(chǎn)黨軍隊這一稱呼,在抗日戰(zhàn)爭中,日軍都不這么強調(diào),現(xiàn)在更不必特別強調(diào)。
抗日戰(zhàn)爭史料之浩瀚,令人難以想象
在談到為什么把《抗日戰(zhàn)爭》作為戰(zhàn)爭系列的最后一部來寫時,王樹增說,沒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難寫了。
第一個難度,史料之浩瀚令人難以想象。搜集整理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五年,因為王樹增的戰(zhàn)爭系列不是寫一本收集一本,是二十多年以來他一直關(guān)注整個戰(zhàn)爭系列所有的檔案史料,相比其他作品而言,《抗日戰(zhàn)爭》在史料的查證、收集、采訪和運用上的難度最大。實際上,無論是正面戰(zhàn)場還是敵后戰(zhàn)場,我們這么多年來對這場戰(zhàn)爭的檔案的整理留存,口述歷史的留存等等都做得不夠。王樹增感嘆,我們遺忘的太多了,對那些在這場戰(zhàn)爭當(dāng)中為這個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對這段歷史也不公平。在搜集資料時,王樹增還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東方人治史不嚴謹,虛妄的太多,可信度不高。很多歷史表述,判斷比較多,數(shù)據(jù)一看就是離譜的,普通讀者看不出來,但研究者看深了看多了就知道這是離譜的。所以必須去做很多去偽存真的工作,這個工作是讓王樹增耗費時間最多的內(nèi)容。
第二個難度是認知的問題。王樹增坦率地講,至少他腦子里對抗日戰(zhàn)爭的認知和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樣的。他說:“毋庸諱言,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抗戰(zhàn)史的表述實際上是有偏頗的。這種偏頗也造成了今天廣大的中國讀者對抗日戰(zhàn)爭的某些認識往往形成輿論的焦點和熱點。這些遺留下來的歷史話題、輿論話題,至今還在熱議不衰。我不敢說回應(yīng)讀者的疑點,但我盡量靠近讀者。我知道讀者心里在想什么,盡可能地靠近他們的心里。”
現(xiàn)在,《抗日戰(zhàn)爭》的第三卷還在校對中。王樹增說,所謂校對,并不是校對正文,而是校對書的注釋。有的讀者需要注釋,光這個注釋,要重新合一遍,把原出處找出來再核對一遍,沒有兩三個月是完不成一卷的,而且非常繁雜。他希望不要出錯,一點兒錯都不要出。
三卷本的《抗日戰(zhàn)爭》,僅記者拿到手的第一卷就有60萬字。在快餐式、碎片化閱讀流行的當(dāng)下,讀者,尤其是王樹增非常期待的青年讀者能讀進去嗎?王樹增自己也很忐忑,他對記者說:“我們干這行跟你們一樣,壓力特別大,有時不敢進書店,心里沒底氣,憑什么讓讀者拿真金白銀去買你的書?”
但另一方面,王樹增又充滿了自信。《抗日戰(zhàn)爭》中,開篇是一個特殊的序章,共7萬字。他說:“你只要耐心地讀完序章,你就會希望把三卷都讀完,絕不會半途扔了。我有這個信心,因為我真心面對讀者,認真地為他們寫作,功夫下到了。”
王樹增說,現(xiàn)在的快速閱讀、手機閱讀,各有好處,適合現(xiàn)代生活的節(jié)奏,反對也沒有用。但他一直有個主張,閱讀要多元化,沉下心來的閱讀很有必要。《抗日戰(zhàn)爭》他本不想寫太厚,厚不是他的追求。但關(guān)鍵是題材,薄了還寫不了。
值得欣慰的是,王樹增看到了他辛苦創(chuàng)作的回報。有一次他在遵義講課,書城銷售部門聽說他來了,想要搞簽售。王樹增當(dāng)時挺為難,如果沒有人買多尷尬,他就特不愿意去。但勉強去了以后發(fā)現(xiàn),很多人已經(jīng)排上隊了,那天還下著小雨,排隊的絕大部分是年輕人。當(dāng)時簽售的正是他的大部頭著作《長征》。王樹增當(dāng)場就跟書城的老板說,今天打折,你要不愿意,錢我來補,孩子們掙錢不容易。他說:“當(dāng)時我非常感動,真是看到上帝了。每一個年輕讀者都是我的上帝,我就是寫給你們的。”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