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用開(kāi)闊之地承載歷史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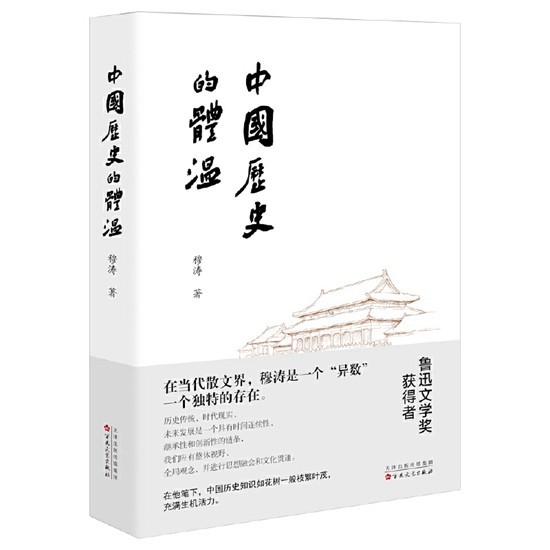
作為一本散文家之書(shū),更多值得探尋的,是藏于幽微細(xì)節(jié)之處對(duì)普遍規(guī)律與人性稟賦的洞察,那是作者與讀者建立聯(lián)系的秘密通道。
——————————
春天是讀書(shū)天,風(fēng)從陽(yáng)臺(tái)拐個(gè)彎吹進(jìn)室內(nèi),與身體發(fā)膚接觸的瞬間,涼中帶暖,且攜帶了春草與春樹(shù)的氣味,令人心曠神怡,要不“春風(fēng)拂面”這4個(gè)字,怎會(huì)常被用來(lái)形容愉悅與舒服?
讀的是散文家穆濤先生所著《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內(nèi)容風(fēng)格明顯是“大散文”,但字里行間時(shí)而蹦出一兩句“俏皮話”,又在提示讀者,這是拐過(guò)彎的表達(dá)方式,如春風(fēng)過(guò)陽(yáng)臺(tái),消弱了速度,增加了溫度與氣味,在保證文本的嚴(yán)肅與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不受損的同時(shí),可以提高閱讀的趣味性。
這幾年讀歷史書(shū),對(duì)“歷史的溫度”這一說(shuō)法頗有共鳴,歷史如果是條長(zhǎng)河的話,那么用溫度作為度量衡,便會(huì)發(fā)現(xiàn)有的階段沸若巖漿,有的階段冷若冰霜,總之讓人感覺(jué)到舒適溫度的階段,不多且不長(zhǎng)。《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找到了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歷史的關(guān)鍵詞——“體溫”,這是一個(gè)非常妥帖的角度,人類標(biāo)準(zhǔn)體溫約為37℃,某一段歷史如果能夠保持這一觸感溫度,想必也是現(xiàn)代人最想穿越回去的時(shí)代了吧。
《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主要篇章以《漢書(shū)》《史記》為參考對(duì)象,對(duì)漢代的人與事進(jìn)行了一番打量。閱讀這本書(shū),對(duì)3個(gè)人有了更深的印象。其一是董仲舒,漢武帝劉徹與他,以通信的方式三問(wèn)三答,“天人三策”的過(guò)程中,兩人相互試探、彼此尊重,董仲舒深諳“直言有諱”的職場(chǎng)情商,與上司進(jìn)行了一場(chǎng)高質(zhì)量對(duì)話。作者穆濤在寫(xiě)作相關(guān)章節(jié)時(shí),曾尋訪位于西安城北策村的董仲舒墓,古今兩位讀書(shū)人在此有了一次無(wú)形的交集,穆濤用本書(shū)罕見(jiàn)的大段感性文字表達(dá)了對(duì)董仲舒的看法。
其二是劉濞,劉邦在冊(cè)封他這位侄子時(shí),忍不住說(shuō)了一句“一看你就天生帶著謀反的小樣兒”(“若狀有反相”——《史記·吳王濞列傳》),穆濤也在書(shū)中寫(xiě)到“劉濞不太具備一個(gè)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質(zhì),性格外露,腦子不夠清醒,執(zhí)拗任性,甚至還有點(diǎn)一根筋”,但傻人有蠻勁,劉濞在封地仗著銅礦與海鹽資源,大肆偷鑄銅錢(qián)、生產(chǎn)海鹽,把自己和吳國(guó)老百姓的小日子搞得有聲有色。劉濞的一生是被懷疑的一生,他后來(lái)發(fā)動(dòng)“七國(guó)之亂”,更像是賭氣行為,但確實(shí)這個(gè)人志大才疏,劉邦對(duì)他的懷疑與鄙視,是正確的。
其三是劉邦,劉邦的故事有許多,但他為老父親劉煓所做的一件事,還是足見(jiàn)其性格特征。劉煓當(dāng)了太上皇,還是悶悶不樂(lè),劉邦問(wèn)及原因,才知道父親是想念老家了——按穆濤的說(shuō)法是,對(duì)“農(nóng)家樂(lè)”生活念念不忘。于是劉邦在今天西安臨潼的東北方向,按照沛郡豐邑(今江蘇徐州豐縣)的樣子,原樣復(fù)制了一個(gè),后來(lái)被稱為“新豐”城邑,“家鄉(xiāng)父老搬過(guò)來(lái)后,不僅人,連犬羊雞鴨都走不錯(cuò)家門(mén)”。
讀到穆濤對(duì)這些人與事的描寫(xiě),總是會(huì)忍俊不禁。有一種幽默是深藏不露的,它不見(jiàn)于詞句,也不顯露于“脫口秀”式的表達(dá),而在于選擇的角度和敘述的方式。通過(guò)《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中有關(guān)人物的描寫(xiě),可以觀察和感受到歷史人物作為普通人的一面,董仲舒的“文化人范兒”,劉濞的“歡樂(lè)喜劇人形象”,劉邦“可以說(shuō)他沒(méi)文化,但他是個(gè)大孝子”……當(dāng)歷史人物散發(fā)出“人味兒”,他們不但自身具備了溫度,也讓承載著他們故事的書(shū)頁(yè)有了溫度,如此,當(dāng)讀者通過(guò)這樣的方式去觸碰歷史的時(shí)候,便不會(huì)產(chǎn)生被燙到或冰到的感覺(jué)了。
《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中除了寫(xiě)到人,筆觸揮灑令人印象同樣深刻的,當(dāng)屬對(duì)節(jié)氣與自然的描寫(xiě)。作者用著迷般的寫(xiě)法,去詮釋端午節(jié)為何是古代的“國(guó)家防疫日”,此章節(jié)信息量之大,以及寫(xiě)作態(tài)度之端詳,讓這部分內(nèi)容擁有一股攝人的儀式感,同樣,董仲舒對(duì)于雨雹形成的講解,融合了政治、文化、風(fēng)水、地理等諸多要素,邏輯道理渾然天成,用網(wǎng)絡(luò)上流行的說(shuō)法是,充滿了“科技與狠活”;對(duì)于“主氣與客氣”的解讀,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條理分明,主氣好理解——一年二十四個(gè)節(jié)氣便是主理一年四時(shí)的基本氣象,客氣便復(fù)雜了,方方面面,涉及到古代天文學(xué)范疇以及古代哲學(xué)的軸心地帶,中國(guó)人對(duì)天地細(xì)致入微的觀察,均可在主氣與客氣那里找到對(duì)應(yīng)與落腳點(diǎn)……
《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書(shū)名自帶分量與重量,但散文家書(shū)寫(xiě)歷史,通常會(huì)用一片開(kāi)闊之地來(lái)承載歷史的分量與重量,歷史學(xué)家可以用散文家的筆調(diào)來(lái)寫(xiě)歷史,散文家自然也可以用歷史學(xué)家的口吻寫(xiě)歷史,兩種身份的交叉與跨界,均會(huì)帶來(lái)閱讀感受的化學(xué)反應(yīng)。《中國(guó)歷史的體溫》作為一本散文家之書(shū),在讓人領(lǐng)略“大散文”之美的同時(shí),更多值得探尋的,是藏于幽微細(xì)節(jié)之處對(duì)普遍規(guī)律與人性稟賦的洞察,那是作者與讀者建立聯(lián)系的秘密通道。
韓浩月

賬號(hào)+密碼登錄
手機(jī)+密碼登錄
還沒(méi)有賬號(hào)?
立即注冊(cè)